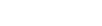城市文化與城市形象
時(shí)間:
高小康1由 分享
一、城市形象的文化意義
幾年前,許多城市先后展出了一種名為《大地走紅》的環(huán)境藝術(shù),就是用幾萬(wàn)把紅傘把公園裝飾起來(lái),形成一種供人欣賞的景觀。但很快這一藝術(shù)就產(chǎn)生了一種事先誰(shuí)也沒(méi)有料到的效應(yīng):它在每個(gè)城市的展出幾乎都變成了一個(gè)引人注目的公共話題。話題就集中在市民們觀賞這些露天展放的紅傘時(shí)的行為方面。在許多城市里,這種展出的后果可以說(shuō)成是“慘不忍睹”:幾萬(wàn)把紅傘被前來(lái)參觀的市民們偷的偷、搶的搶、糟蹋的糟蹋,最后一片狼藉。而在有的城市里展出的情況卻出奇地好,參觀的市民秩序井然,紅傘無(wú)一丟失,也幾乎無(wú)人為的損壞。這種反差的出現(xiàn)可能有幾分偶然,但對(duì)于傳媒來(lái)說(shuō)就不是這么簡(jiǎn)單了。這件事被與此事有關(guān)的城市當(dāng)?shù)貍髅揭暈橐患憩F(xiàn)本地市民素質(zhì)的大事盡力渲染,在一些城市的市民當(dāng)中的確引起了一些震動(dòng)。這件事因此而成為影響一個(gè)城市聲譽(yù)的事件,有的城市為本市市民的良好表現(xiàn)而自豪,有的城市則感到有幾分尷尬,似乎自己出了丑??偠灾?,這個(gè)事件使許多城市注意到了一個(gè)東西,就是城市的形象問(wèn)題。
現(xiàn)代文化的發(fā)展從總的趨勢(shì)來(lái)講就是都市化,人們的生存乃至全部生活方式都以都市為中心輻湊、匯聚了起來(lái)。在這個(gè)輻湊、匯聚的過(guò)程中,都市不僅在物質(zhì)上、空間上發(fā)展得越來(lái)越多、越來(lái)越大,而且在這個(gè)發(fā)展過(guò)程中,都市文化對(duì)居住在都市中的市民形成了一股凝聚力。當(dāng)一個(gè)城市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把居民凝聚成一個(gè)文化上的統(tǒng)一體時(shí),便構(gòu)成了一個(gè)城市本身的形象。
城市形象不是當(dāng)代文化特有的現(xiàn)象,歷史上每一個(gè)偉大的城市可以說(shuō)都有自己鮮明的形象:伯里克利的雅典[1]以輝煌的衛(wèi)城建筑、民主的公眾生活、完美的悲劇藝術(shù)以及偉大的蘇格拉底構(gòu)筑起了這個(gè)城市彪炳千古的形象;奧古斯都的羅馬則是以宏大的競(jìng)技場(chǎng)和水道、高貴而又殘忍的羅馬公民、所向無(wú)敵的帝國(guó)軍人構(gòu)成了不可一世的羅馬形象;維多利亞的倫敦形象是霧氣沉沉的天空、泥濘的街道、一本正經(jīng)的商人和衣冠楚楚的紳士;“云里帝城雙鳳闕,雨中春樹萬(wàn)人家”是盛唐時(shí)代的長(zhǎng)安形象;“有三秋桂子,十里荷花”是北宋盛期的杭州;而“江南佳麗地,金陵帝王州”則是曾為十朝故都的南京……城市形象顯示著城市的個(gè)性,也成為凝聚市民精神的力量。古雅典黃金時(shí)代的執(zhí)政伯里克利在追悼陣亡將士時(shí)所作的一篇演講就是一個(gè)鼓吹城市精神的例子:
我們的制度是別人的模范,而不是我們模仿任何其他的人的……當(dāng)我們的工作完畢的時(shí)候,我們可以享受各種娛樂(lè),以提高我們的精神。整個(gè)一年之中,有各種定期賽會(huì)和祭祀;在我們的家庭中,我們有華麗而風(fēng)雅的設(shè)備,每天怡娛心目,使我們忘記了我們的憂慮。我們的城邦這樣偉大,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東西都充分地帶給我們……
……這就是這些人為它慷慨而戰(zhàn)、慷慨而死的一個(gè)城邦,因?yàn)樗麄冎灰氲絾适Я诉@個(gè)城邦,就不寒而栗。很自然地,我們生于他們之后的人,每個(gè)人都應(yīng)當(dāng)忍受一切痛苦,為它服務(wù)。[2]
這篇演講是用城市形象來(lái)激發(fā)公民的自豪感,團(tuán)結(jié)、凝聚公民精神的典范。伯里克利的雅典并不是唯一能夠使公民感到自豪的城市,事實(shí)上,每一個(gè)偉大的城市都具有這種形象的凝聚力。正是靠著這種凝聚力,一個(gè)都市才有可能成為偉大的城市,才有可能在政治、經(jīng)濟(jì)和文化各方面發(fā)展起來(lái)。只是在當(dāng)代這樣一個(gè)比過(guò)去更加關(guān)注形象、更加依賴著形象而生存的文化環(huán)境中,城市形象變得比以往任何時(shí)候都具有更加重要、也更加實(shí)際的意義。
1955年,澳大利亞的悉尼市通過(guò)一次國(guó)際建筑設(shè)計(jì)競(jìng)賽選中了一個(gè)奇形怪狀的建筑設(shè)計(jì)方案,而后花了近二十年的時(shí)間和幾乎相當(dāng)于預(yù)算二十倍的費(fèi)用才建成了這座建筑。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悉尼歌劇院。從建筑設(shè)計(jì)的角度和具體使用的效果來(lái)看,這座建筑的效果決不是無(wú)可挑剔的。然而這座建筑自有它不可替代的價(jià)值。近幾十年來(lái),悉尼的地位越來(lái)越高,使得堪培拉、墨爾本等城市都感到嫉妒。而悉尼地位的上升與這座歌劇院有不可分割的聯(lián)系。有人說(shuō),悉尼歌劇院每年在無(wú)形中為悉尼作了上百億美元的廣告。無(wú)法斷定這種說(shuō)法是否有點(diǎn)夸大其詞,但有一點(diǎn)是可以肯定的,那就是悉尼歌劇院大大提升了悉尼的城市形象,而這種提升了的城市形象的確為悉尼帶來(lái)了巨大的文化和經(jīng)濟(jì)效益。
時(shí)至今日,人們要提到悉尼,首先會(huì)想到的就是那座歌劇院。悉尼的城市形象就是以這座歌劇院為標(biāo)志。諸如此類的城市形象標(biāo)志可以找到很多──巴黎的凱旋門和埃斐爾鐵塔、紐約的自由女神塑像和世界貿(mào)易中心大廈雙塔、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、北京的天安門等等。這些實(shí)實(shí)在在的建筑物使得一個(gè)城市的形象變得鮮明具體,可以給人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。但這只是城市形象的一部分,即靜態(tài)的、物質(zhì)的或者說(shuō)是“硬件”的部分,還遠(yuǎn)遠(yuǎn)不是城市形象的全部,甚至往往還不能算是城市形象的主要部分。
城市形象的主要部分在于它的動(dòng)態(tài)的、富于活力的“軟件”部分。這就是一個(gè)城市中的人文氛圍。有一位學(xué)者在講到梅特涅時(shí)代的維也納時(shí)這樣寫道:
在任何一個(gè)認(rèn)真的旁觀者看來(lái),維也納人似乎永遠(yuǎn)沉溺在狂歡鬧飲之中。吃、喝和尋歡作樂(lè)是維也納人的三種基本的德行和快樂(lè)。他們永遠(yuǎn)在過(guò)周末,永遠(yuǎn)在過(guò)狂歡節(jié)。到處是音樂(lè)。無(wú)數(shù)的酒館里無(wú)論白天黑夜擠滿了酩酊酒鬼。到處是成群的紈绔子弟和衣著入時(shí)的妙齡少女。無(wú)論何處,無(wú)論是日常生活、藝術(shù)還是文學(xué)中,流行的都是優(yōu)雅機(jī)智的玩笑。對(duì)維也納人來(lái)說(shuō),世界上一切事情中最要緊的事就是他們能夠開個(gè)玩笑。[3]
這里所描述出來(lái)的維也納,完全是一副頹廢的形象,而這個(gè)形象的形成不是它的建筑或其他“硬件”條件的變化,而是人文氛圍起了變化。維也納城市建筑的風(fēng)貌也許很多年都不會(huì)有根本性的變化,而這座城市的整體形象卻會(huì)隨著人文氛圍的變化而變化。
再比如中國(guó)古代宋元時(shí)期的杭州,被當(dāng)時(shí)人稱為“銷金鍋兒”。這就是當(dāng)時(shí)杭州的形象。而這個(gè)形象更是與人的活動(dòng)密切相關(guān)的。馬可·波羅對(duì)杭州的描寫是:“行在(按指杭州)之大,舉世無(wú)匹。一個(gè)人可以在那里尋到這么多的樂(lè)子,簡(jiǎn)直恍若步入天堂。”[4]這個(gè)在中國(guó)與蘇州并稱為“天堂”的城市,它的魅力決不僅僅在于自然的湖光山色,更重要的是南宋以來(lái)商業(yè)的繁榮所帶給這個(gè)城市的消費(fèi)文化形象,即所謂“銷金鍋兒”。馬可·波羅所說(shuō)的“可以在那里尋到這么多的樂(lè)子”的真實(shí)含義也就在這里。“水光瀲滟晴方好,山色空濛雨亦奇”只是杭州形象的不變的底色,而真正的城市形象卻是在人文氛圍的變遷中形成和發(fā)展變化的。所謂“淡妝濃抹總相宜”只有從人文環(huán)境的變化方面講才能夠顯示出城市形象變化的意義。
維也納也好,杭州也好,這些城市形象的人文氛圍方面都明顯地顯示出娛樂(lè)文化的特點(diǎn),這似乎應(yīng)當(dāng)算作那一類奢華、頹廢的消費(fèi)型城市的特點(diǎn)。確實(shí),梅特涅時(shí)代的維也納和“暖風(fēng)熏得游人醉,直把杭州作汴州”的南宋朝廷統(tǒng)治下的杭州有幾分相似,都帶點(diǎn)頹廢氣。但這并不意味著娛樂(lè)文化對(duì)于形成城市形象的作用只是發(fā)生在這些頹廢的城市上。一個(gè)城市形象的“軟件”部分,即那些生氣勃勃的、最能夠感染人影響人的部分,主要就是表現(xiàn)在城市的娛樂(lè)文化方面。從古雅典的半圓形劇場(chǎng)、古羅馬的大競(jìng)技場(chǎng)直到現(xiàn)代城市爭(zhēng)相攀比的標(biāo)志性公共設(shè)施──大型體育館、歌劇院、游樂(lè)場(chǎng)等等,都體現(xiàn)出娛樂(lè)活動(dòng)在一個(gè)城市的形象中所具有的突出位置。從某種意義上講,一個(gè)城市的活形象,就在于它的娛樂(lè)活動(dòng)的方式。
二、市民與城市的關(guān)系
周密在《武林舊事》中曾講到南宋時(shí)期杭州人所享受的種種好處:
若住屋則動(dòng)蠲公私房賃,或終歲不償一環(huán)。諸務(wù)稅息,亦多蠲收,有連年不收一孔者,皆朝廷自行抱認(rèn)。諸項(xiàng)窠名,恩賞則有黃榜錢,雪降則有雪寒錢,久雨久晴則又有賑恤錢米,大家富室則又隨時(shí)有所資給,大官拜命則有所謂搶節(jié)錢,病者則有施藥局,童幼不能自育者則有慈幼局,貧而無(wú)依者則有養(yǎng)濟(jì)院,死而無(wú)殮者則有漏澤園。民生何其幸歟!
這里講到當(dāng)時(shí)杭州官府給民眾的種種好處,而后感慨生在杭州的居民何其幸運(yùn)?;蛟S一個(gè)城市的市民所享受到的好處并不一定與其他城市相當(dāng),然而只要是一個(gè)繁榮、成功的城市,總歸會(huì)使市民產(chǎn)生一種作為這個(gè)城市一員的自豪與幸運(yùn)之感。這就是古代雅典、羅馬等偉大的城市所培養(yǎng)的“公民”意識(shí)和今天的許多大都市市民的“ 都市人”意識(shí)。這種作為一個(gè)城市市民的自豪與幸運(yùn)感,就是依附、凝聚于城市形象上的城市精神。
這樣一種城市形象對(duì)于在城市中生活的市民個(gè)體有什么意義呢?那種使市民足以引為驕傲的城市形象實(shí)際上是在為市民個(gè)體提供著一種共享性質(zhì)的生存體驗(yàn)。伯里克利在談到雅典公民的特點(diǎn)時(shí)說(shuō):“一個(gè)不關(guān)心政治的人,我們不說(shuō)他是一個(gè)注意自己事務(wù)的人,而說(shuō)他根本沒(méi)有事務(wù)。”[5]這就是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所提供給每一個(gè)城邦權(quán)利和義務(wù),也是城市中“公民”意識(shí)的起源。這種“公民”用亞里斯多德的話來(lái)說(shuō)叫做“政治動(dòng)物”。不過(guò)伯里克利和亞里斯多德在這里所說(shuō)的“政治”一詞不能用后來(lái)的階級(jí)統(tǒng)治觀念來(lái)解釋。這里的“政治”只能被理解為“城邦事務(wù)”。“政治動(dòng)物”意味著公民在存在的本質(zhì)上與城邦或城市的一體性。在血緣關(guān)系統(tǒng)治的社會(huì)中,個(gè)人的存在意義和價(jià)值是通過(guò)與血緣鏈的維系而實(shí)現(xiàn)的,祖宗和后代構(gòu)成了他生存關(guān)懷的基本目的;在階級(jí)關(guān)系統(tǒng)治的社會(huì)中,個(gè)人存在是服從于社會(huì)等級(jí)秩序的,因而不存在脫離階級(jí)體系的個(gè)人化的意義關(guān)系。而在一個(gè)雅典式的城邦或城市社會(huì)中,個(gè)人的存在是通過(guò)與整個(gè)城市的一體性存在實(shí)現(xiàn)的。按照伯里克利的說(shuō)法,雅典城邦中個(gè)人的價(jià)值是被城邦充分承認(rèn)的,這個(gè)價(jià)值就是自由:“要自由才能有幸福,要勇敢才能有自由。”這就是說(shuō),雅典人的價(jià)值不是天賦的,也不是他人給定的,而是通過(guò)“勇敢”──即個(gè)人作為城邦公民的行動(dòng)──而獲得的。反過(guò)來(lái)說(shuō),城邦的存在其實(shí)也是通過(guò)個(gè)人的“勇敢”而實(shí)現(xiàn)的。當(dāng)一個(gè)人在實(shí)現(xiàn)自己的時(shí)候也是在實(shí)現(xiàn)城邦,當(dāng)他為城邦效力的時(shí)候也就是在實(shí)現(xiàn)自己。這就是個(gè)人與城邦或城市的意義共享關(guān)系。
古雅典的城邦民主制在政治制度史上只能算是一個(gè)個(gè)別的例子,但在這種城邦制度下培養(yǎng)出來(lái)的公民意識(shí)卻是后代城市意識(shí)的源泉。一個(gè)城市的市民對(duì)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感到自豪和自信的時(shí)候,他正是在表達(dá)一種把他個(gè)人與城市在情感和價(jià)值上結(jié)問(wèn)一體的需要??梢哉f(shuō),一個(gè)城市是否有內(nèi)在的活力,就是看它的市民是不是為它感到自豪和自信,是不是真正與這個(gè)城市的傳統(tǒng)、與它的精神一體化了。小說(shuō)《儒林外史》中有這樣一個(gè)細(xì)節(jié):兩名挑著糞桶賣糞的挑夫互相商量道,今天的貨賣完了后就喝口水,上雨花臺(tái)看落照去。文人聞之后不禁感嘆道,菜傭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!這就是說(shuō),南京作為六朝故都的氣象已滲透到包括菜傭酒保在內(nèi)的普通市民精神深處,使市民從精神氣質(zhì)上與這座城市、與它的形象一體化了。
當(dāng)代城市比起伯里克利時(shí)代的城邦當(dāng)然遠(yuǎn)遠(yuǎn)不同了,即使與后來(lái)晚近得多的古典城市相比,也有了很大的差異。與過(guò)去相比一個(gè)重要的差別是城市居民的情況變得復(fù)雜多了。近年來(lái)在許多城市中發(fā)生過(guò)而且還在繼續(xù)發(fā)生著馬路上的窨井蓋被盜的事情。偷盜窨井蓋的行為除了作為一般盜竊犯罪的動(dòng)機(jī)之外,還意味著偷盜者與城市關(guān)系的疏遠(yuǎn)。因?yàn)閷?duì)于一般人來(lái)說(shuō),偷盜窨井蓋比起其他盜竊行為來(lái),風(fēng)險(xiǎn)和犯罪感的心理閾限要低得多,利益的誘惑也同樣低;與此同時(shí),窨井蓋被盜對(duì)市民生活的影響卻很明顯。因此,一般說(shuō)來(lái)偷盜窨井蓋的誘惑力應(yīng)該不是很大。那么為什么會(huì)發(fā)生這樣多的窨井蓋被盜的事件呢?根據(jù)調(diào)查了解的結(jié)果得知,絕大多數(shù)偷盜窨井蓋的事是城市里的流動(dòng)人口所為。這部分人與城市的關(guān)系當(dāng)然是比較疏遠(yuǎn)的。當(dāng)“大地走紅”展出在上海、天津之類的大都市遇到被哄搶、偷盜或故意損壞的尷尬局面時(shí),人們也發(fā)現(xiàn)問(wèn)題主要出在流動(dòng)人口的身上。顯然,當(dāng)代都市中的流動(dòng)人口是一個(gè)挺麻煩的問(wèn)題。這些人與城市很少能產(chǎn)生共享性,因而發(fā)生那些尷尬局面似乎也是無(wú)可奈何之事。
然而在這種事件的發(fā)生中,往往也可以看出市民態(tài)度的冷漠。比如在南京,城市的管理機(jī)構(gòu)為了方便市民、進(jìn)一步親和城市與市民的關(guān)系,曾在許多交通管理地點(diǎn)準(zhǔn)備了大量“便民傘”,無(wú)償提供給市民借用。但不出一年,這些“便民傘”中的絕大部分一去不返。據(jù)說(shuō)造成這種尷尬的原因也與流動(dòng)人口有關(guān),然而那種帶著顯眼標(biāo)志的“便民傘”被人隨意攜帶離開南京或留作己物而無(wú)人過(guò)問(wèn),說(shuō)明市民對(duì)這種事件抱著聽之任之的冷漠態(tài)度。事實(shí)上,窨井蓋和紅傘被盜之類的事情發(fā)生或得不到制止,也不能說(shuō)與一般市民的冷漠態(tài)度無(wú)關(guān)。在許多城市里要找到諸如“便民傘”散失之類的于社會(huì)公德有虧的問(wèn)題實(shí)在容易。人們通常把這種現(xiàn)象歸因于市民文化素質(zhì)的問(wèn)題。這當(dāng)然是問(wèn)題的一個(gè)方面,但還有更深遠(yuǎn)的原因。伯里克利時(shí)代的雅典是雅典人的驕傲,而在當(dāng)代,許多人在提到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城市時(shí),口氣常常是批評(píng)的甚或自卑的。這好象是一種謙虛的美德,然而也可以看出當(dāng)代城市中市民在感情上與城市的疏遠(yuǎn)。當(dāng)代人在與他人交流時(shí),通常注意表現(xiàn)的是自己的個(gè)人身份──職業(yè)、地位等等,而很少想到自己還是某個(gè)城市的市民,除非是某些具有特殊地位的城市可以使他獲得別人的尊敬,比如在七十年代上海人之于其他小城市的人、八十年代廣州人之于北方開放較晚的城市中人。如果沒(méi)有這種特殊的等級(jí)意識(shí),人們就很難意識(shí)到自己作為某城市市民的身份。市民對(duì)城市事務(wù)的冷漠從根本上說(shuō)就在于市民與城市關(guān)系的游離。
三、主流文化圈與城市精神
在中國(guó),本世紀(jì)發(fā)展起來(lái)的許許多多大城市中,上海應(yīng)當(dāng)說(shuō)是比較有特色的一個(gè)。與中國(guó)其他許多城市比較,上海的生活方式中與眾不同的特點(diǎn)之一就是喝咖啡。當(dāng)然,如果說(shuō)的是三四十年代,至遲五十年代,或者八九十年代,在中國(guó)的大多數(shù)大都市中,喝咖啡算不上是什么特別的生活習(xí)慣,盡管并不是人人都喜歡。但如果說(shuō)的是六七十年代,尤其是七十年代,情況就不同了。對(duì)于六七十年代的一般中國(guó)人來(lái)說(shuō),喝咖啡、吃西餐、穿西裝之類的生活方式,不消說(shuō)都被當(dāng)作“資產(chǎn)階級(jí)生活方式”而加以拒斥。然而上海卻一直還保留著咖啡店,上海人還在喝咖啡。孤立地看,喝咖啡這件事的確很難看出有什么特別的意義。但如果設(shè)想一下,在全民投入““””,努力倡導(dǎo)思想革命化,狠批“資產(chǎn)階級(jí)生活方式”,肅清一切“封、資、修”流毒的“火藥味”很濃的時(shí)代,同時(shí)也是生活資料高度匱乏、娛樂(lè)活動(dòng)單調(diào)乏味的時(shí)代,有的人卻在悠閑地品啜帶著“小資情調(diào)”的咖啡,豈不是很令人感到奇怪的事嗎?
這就是上海文化的一個(gè)特點(diǎn)。對(duì)于上海人來(lái)說(shuō),喝咖啡、吃西餐并不象其他許多地方那樣被看成是奇風(fēng)異俗。這是從本世紀(jì)初以來(lái)西方人浸染到上海資產(chǎn)階級(jí)的生活習(xí)慣,又通過(guò)上海的資產(chǎn)階級(jí)把這種生活習(xí)慣“傳染”給了一般上海市民。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,各個(gè)大城市過(guò)去的資產(chǎn)階級(jí)都可能有這種生活習(xí)慣。但卻只有上海人把這種習(xí)慣頑強(qiáng)地保留了下來(lái),甚至抵抗住了““””火藥味的沖擊。這個(gè)事實(shí)表明,喝咖啡雖然是件小事,但它標(biāo)志著上海城市文化中一種根深蒂固的東西,這就是自本世紀(jì)初以來(lái)上海以資產(chǎn)階級(jí)、小資產(chǎn)階級(jí)為主的文化圈所奉行的生活方式。這種生活方式不僅作為行為方式影響到了上海市民的各個(gè)階層,而且影響到了他們的習(xí)慣心理,成為上海人特有的風(fēng)俗。
一種生活方式、一種娛樂(lè)方式能夠如此根深蒂固地影響到一個(gè)城市的風(fēng)俗,根據(jù)在于這個(gè)城市有一個(gè)有強(qiáng)大影響力的文化重心,也就是城市中的主流文化圈。一個(gè)城市要能夠凝聚成一種精神、一個(gè)形象,首先要在市民中形成使大眾有所歸趨的主流文化圈。上海自本世紀(jì)二十年代前后中國(guó)資本主義興起之日起便成為中國(guó)資產(chǎn)階級(jí)的大本營(yíng)。由資產(chǎn)階級(jí)和早期商人、士紳等“社會(huì)名流”融合形成的上海社會(huì)的主流文化圈不僅影響著上海的經(jīng)濟(jì)、市政乃至政治生活,更重要的是在整個(gè)城市社會(huì)中人們的觀念里,這個(gè)主流文化圈成為社會(huì)文化的代表,他們的價(jià)值觀念和趣味標(biāo)準(zhǔn)成為社會(huì)公認(rèn)的標(biāo)準(zhǔn)。這樣一個(gè)主流文化圈盡管在后來(lái)從政治和社會(huì)結(jié)構(gòu)的意義上消失了,而他們作為上海文化、尤其是上海趣味的象征卻一直潛藏在上海人觀念的深處。所以即使是在火藥味十足的““””年代,許多上海人仍然渴望著坐在幽暗靜謐的咖啡店里悠悠地品啜。可以想見,人們心理深處所尋求的娛樂(lè)趣味仍然屬于早已灰飛煙滅的那一群群出入于國(guó)際飯店、跑馬場(chǎng)和音樂(lè)廳的社會(huì)名流們。
有一位外國(guó)學(xué)者在研究中國(guó)歷史時(shí)發(fā)現(xiàn)了一個(gè)特點(diǎn):“中華帝國(guó)有一個(gè)不可思議的地方,就是它能用一個(gè)很小的官員編制,來(lái)統(tǒng)治如此眾多的人口。”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(diǎn)呢?他發(fā)現(xiàn):
一般的地方行政官職權(quán)的一個(gè)特點(diǎn),就是他在表面上管轄著一個(gè)約有二十萬(wàn)到五十萬(wàn)居民的地區(qū),地方長(zhǎng)官是中央政府任命的該地唯一代表。這種表面地位造成的結(jié)果,就是地方長(zhǎng)官只有在與當(dāng)?shù)丶澥款^面人物的密切合作下,才能做他的工作。[6]
就是說(shuō)中國(guó)的行政管理傳統(tǒng)上主要不是靠官吏直接操作,而是靠社會(huì)名流的協(xié)助進(jìn)行。一般地區(qū)的行政管理是如此,城市管理同樣如此,因而中國(guó)傳統(tǒng)的城市中主流文化圈就由這些社會(huì)名流構(gòu)成。從明清時(shí)期士人與商人結(jié)合形成的“紳商”階層到后來(lái)上海的資產(chǎn)階級(jí),都具有這種社會(huì)名流的傳統(tǒng)地位、實(shí)力和影響力。
中華人民共和國(guó)成立后,中國(guó)城市的管理不再是傳統(tǒng)的社會(huì)名流的事,而是各級(jí)行政機(jī)構(gòu)和單位組織的事。在這種管理方式下,城市市民的價(jià)值觀念和趣味標(biāo)準(zhǔn)受到各級(jí)單位組織、行政管理部門和政府傳播媒介的輿論引導(dǎo),形成了一種具有意識(shí)形態(tài)特征統(tǒng)一性的城市形象。這種類型的城市生活中沒(méi)有什么特殊的社會(huì)名流階層,因而也沒(méi)有獨(dú)立的主流文化圈,只有滲透在社會(huì)各個(gè)階層中的管理結(jié)構(gòu)與管理機(jī)制在起著引導(dǎo)或制約的作用。
這種管理方式從理論上講一直是延續(xù)的,但對(duì)城市市民的精神、趣味的引導(dǎo)作用卻隨著城市社會(huì)的走向開放而逐漸消退著。當(dāng)各級(jí)政府和單位組織不再對(duì)市民的趣味進(jìn)行有意識(shí)和有效率的引導(dǎo)時(shí),市民的生活方式開始走向了隨機(jī)發(fā)展的趨勢(shì),由于這種發(fā)展的隨機(jī)性,城市形象也隨之變得破碎和模糊起來(lái)。在這種城市生活的環(huán)境中,沒(méi)有穩(wěn)定的、有物質(zhì)力量和號(hào)召力的主流文化圈影響和引導(dǎo)市民精神與趣味的發(fā)展,市民的生活方式便走向自發(fā)地接受隨機(jī)引導(dǎo)的方向。最典型的發(fā)展方式就是變得時(shí)尚化了:人們的趣味、愛好和評(píng)價(jià)標(biāo)準(zhǔn)都失去了穩(wěn)定性和一貫性,一時(shí)興起的時(shí)髦會(huì)改變整個(gè)城市的形象。由時(shí)尚制造出來(lái)的城市形象其實(shí)是一種畸象,它使得市民失去了對(duì)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這個(gè)城市的真正感覺,沒(méi)有了一個(gè)完整、清晰的城市形象概念,只有不停地隨波逐流變換著的社會(huì)風(fēng)氣。在一個(gè)沒(méi)有了完整形象的城市里生活,人們當(dāng)然無(wú)法產(chǎn)生對(duì)這個(gè)城市的愛,甚至無(wú)法產(chǎn)生對(duì)城市本身的起碼關(guān)注。冷漠與游離便是在所難免的事了。
四、狂歡與城市形象的凝聚
市民與城市關(guān)系的游離應(yīng)當(dāng)說(shuō)是城市文化發(fā)展中的一個(gè)根本性的危機(jī)。當(dāng)代都市不可能再回到古典城市的模式中去,那么怎樣才能使市民與城市重新結(jié)為一體呢?公眾性的娛樂(lè)活動(dòng)就是當(dāng)代城市解決這個(gè)問(wèn)題的思路。大都市之所以都那么熱心于爭(zhēng)辦大型娛樂(lè)活動(dòng),從城市文化建設(shè)的角度來(lái)講,就在于這類活動(dòng)對(duì)于維系城市與市民的精神聯(lián)系具有無(wú)法替代的作用。一個(gè)當(dāng)代都市中可以有幾百萬(wàn)甚至上千萬(wàn)人口,人們的興趣愛好和精神境界的差異是無(wú)法彌合甚至幾乎是無(wú)法溝通的。然而,一場(chǎng)大型運(yùn)動(dòng)會(huì)不僅可能給城市帶來(lái)可觀的商業(yè)利益,與此同時(shí)它將成為一種充滿刺激的情緒場(chǎng),把市民吸引或裹挾進(jìn)來(lái)。這種情緒場(chǎng)對(duì)于大眾來(lái)說(shuō),具有一種原始的圖騰崇拜意味,通過(guò)近乎非理性的激情狂熱使市民得到情緒上的溝通和認(rèn)同。只有在這種全民性的大型娛樂(lè)活動(dòng)中,城市才會(huì)暫時(shí)地消解掉它的多義性和多功能性,變成一個(gè)單一的活動(dòng)群落。
公眾性質(zhì)的娛樂(lè)活動(dòng)中,最典型的傳統(tǒng)形式就是節(jié)日。從某種意義上講,節(jié)日與當(dāng)代城市中新的公眾娛樂(lè)活動(dòng)──大型運(yùn)動(dòng)會(huì)有相似之處,都是群體共享性質(zhì)的狂歡活動(dòng)。一般說(shuō)來(lái),傳統(tǒng)意義上的節(jié)日是以民族或地域社區(qū)為一體形成特定的節(jié)日觀念與節(jié)日形式的。以城市為單位,體現(xiàn)城市特色,作為城市形象展現(xiàn)方式的節(jié)日是一種較特殊的節(jié)日活動(dòng)。
傳統(tǒng)意義上的節(jié)日從本質(zhì)上講都是狂歡,也就是說(shuō)是對(duì)日常生活狀態(tài)的有序性的反叛。傳統(tǒng)的節(jié)日所表達(dá)的、所尋求的是整個(gè)文化群落在自然意義上的共享和一體化狀態(tài)。從這個(gè)意義上看,傳統(tǒng)節(jié)日的實(shí)質(zhì)是反城市的:它通過(guò)狂歡狀態(tài)否定城市對(duì)人的內(nèi)在與外在狀態(tài)的雙重限制,即否定了城市人的教養(yǎng)等級(jí)和權(quán)利分配差異,否定了文化層次,使市民重新回歸為人群。這種傳統(tǒng)節(jié)日形態(tài)的最極端、最標(biāo)準(zhǔn)的形式可以從世界上許多民族習(xí)俗中的狂歡節(jié)活動(dòng)里發(fā)現(xiàn)。
與此同時(shí),當(dāng)代的城市還在發(fā)展著另一種節(jié)日活動(dòng)。這不是傳統(tǒng)的節(jié)日,而是正在不斷被城市“制造”出來(lái)的體現(xiàn)城市自己的個(gè)性的新節(jié)日,如啤酒節(jié)、風(fēng)箏節(jié)、服裝節(jié)、火腿節(jié)之類以及標(biāo)以各種特別名目的藝術(shù)節(jié)。這些節(jié)日產(chǎn)生的根據(jù)當(dāng)然首先是商業(yè)需要。這是當(dāng)代城市為自己做廣告的一種手段,即通過(guò)標(biāo)新立異的節(jié)日名目吸引人們注意,并通過(guò)舉辦相關(guān)的節(jié)日慶典活動(dòng)來(lái)進(jìn)一步擴(kuò)大商業(yè)影響和聯(lián)系。由于商業(yè)動(dòng)機(jī)的驅(qū)動(dòng),舉辦這類節(jié)日如今在許多城市中已成為時(shí)髦,節(jié)日的名目也越來(lái)越離奇。這類節(jié)日中有一些辦得比較成功,能夠持續(xù)較長(zhǎng)的時(shí)間;有的則舉辦不久就難以為繼直至銷聲匿跡;有的甚至剛開始舉辦就失敗了??傊@些節(jié)日都是人為地制造出來(lái)的仿民俗,基本上是一種商業(yè)行為及其產(chǎn)物,決定它的生命力的因素不是傳統(tǒng),而是經(jīng)營(yíng)運(yùn)作水平。
這些商業(yè)性的新節(jié)日當(dāng)然不會(huì)具有什么反城市的意味,相反,它們倒是通過(guò)突出城市的特色來(lái)強(qiáng)調(diào)城市的存在。這些新節(jié)日的基本策劃方式就是以各種手段突出、強(qiáng)化城市形象,也就是說(shuō),新節(jié)日不是反城市而是城市形象的表現(xiàn)方式。如果一個(gè)這樣的新節(jié)日舉辦得很成功,那就是說(shuō)它成功地塑造了這個(gè)城市的形象:在外人看來(lái),這個(gè)節(jié)日顯示出城市的形象特色;在市民看來(lái),節(jié)日激發(fā)了市民對(duì)自己城市形象的自豪與自信。
但一個(gè)靠商業(yè)策劃而制作出來(lái)的節(jié)日從什么意義上能夠稱作城市形象呢?無(wú)論廣告語(yǔ)言怎樣強(qiáng)調(diào)這樣一個(gè)新節(jié)日與城市文化傳統(tǒng)的關(guān)系,它是一個(gè)新制作出來(lái)的東西,這個(gè)事實(shí)本身就表明不是文化傳統(tǒng)自然生成的產(chǎn)物。一個(gè)城市有某種特產(chǎn)或曾經(jīng)有過(guò)某種風(fēng)俗,這同城市形象并不總是一回事。城市形象應(yīng)當(dāng)是城市性格的顯現(xiàn),是一個(gè)城市的文化凝聚力和輻射力的表征。而新節(jié)日所塑造的城市形象其實(shí)是一種商業(yè)形象或者說(shuō)廣告形象,這是一個(gè)城市刻意為自己制造出來(lái)的商業(yè)性外觀,也可以說(shuō)是這個(gè)城市為自己制造的“假面”。換句話說(shuō),一個(gè)商業(yè)性的新節(jié)日實(shí)際上是在為一個(gè)城市制造著假想的城市形象。然而如果經(jīng)營(yíng)成功的話,這個(gè)假想的城市形象本身也會(huì)成為城市市民的一種認(rèn)同方式。人們通過(guò)這個(gè)假想的形象去重新認(rèn)識(shí)和體驗(yàn)這個(gè)城市,從而形成新的城市凝聚力,這正是許多城市的管理、決策層所希望做到的事,只是這個(gè)希望往往不能實(shí)現(xiàn)。因?yàn)樯虡I(yè)性的經(jīng)營(yíng)運(yùn)作如果不能與市民們的激情融合起來(lái),新節(jié)日不能產(chǎn)生傳統(tǒng)節(jié)日那種狂歡節(jié)式的一體化體驗(yàn),這種節(jié)日就只不過(guò)是一種比較大型的廣告而已,隨著廣告畫面的褪色它的魅力也將褪去。歸根到底,城市形象是市民精神的表現(xiàn)而不是一個(gè)簡(jiǎn)單的視覺畫面。
注釋:
[1]嚴(yán)格地說(shuō),雅典城邦是一種國(guó)體而不是一個(gè)城市。但這個(gè)城邦作為一個(gè)小國(guó)家的實(shí)際存在形態(tài)主要是以城市為重心,所以在這里我們?nèi)园阉醋魇且粋€(gè)城市。
[2]引自修昔底德《伯羅奔尼撒戰(zhàn)爭(zhēng)史》130-133頁(yè),商務(wù)印書館1978年版。
[3]譯自F.Willis《Western Civilization》Vol.2,p.167,D.C.Hedth and Company 1981.
[4]引自謝和耐《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(guó)日常生活》29頁(yè),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。
[5]《伯羅奔尼撒戰(zhàn)爭(zhēng)史》132頁(yè)。
[6]費(fèi)正清編《劍橋中國(guó)晚清史》上卷23-24頁(yè),中國(guó)社會(huì)科學(xué)出版社1993年版。